
|
去年在伊斯坦布尔,
废城墙筑通天塔,
长镜头光与影,
海边女人,
古墓园,
车祸,
完。 |

|
平移的运动镜头,物化的精确测量,面无表情的静态状物,不确定的人物、似真似幻的情节都是为了印证“一切都是假话”。以静止人群站立为背景,镜像的巧妙运用很好地平衡了空间,而人物对峙的紧张感凸显了空间结构,相对于其小说,文本被释放到环境,更有独特风貌。节奏适合大提琴的无变奏。 |

|
trompe l'oeil/假象/赝品/梦(一切纯视听情景:装饰物特写 古建筑 停滞的人 镜前自省) ;禁脔/女性的怨恨; 结构的对位;叙事的语焉不详与自相矛盾昭示叙事的虚构属性;双向窥视; 单镜头摇移中位置突变与时间变形;不同速度的时间/心理时间; 视线衔接对象:作为预言者的角色 一种赤裸叙事; 跨时空的声音蒙太奇 |

|
格里耶在创作《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之时,亦构思了《不朽的女人》的剧本。最终雷乃拍摄了前者,于此格里耶借助后者完成了银幕处女秀。两部可视作姐妹篇一并观看。最显著的相似特征:大广场上的静默人群、室内成双男女站立约会等。雕像化的人物强调的仍然是新小说的无人物特征,及无理性的情感状态。创作原型来自格里耶在伊斯坦布尔游览时遇到的一个女人。正如女人就是最好的创作灵感一样。格里耶把记忆通过联想与再现当时情景的融合,并打破与女人在一起的所有时间秩序。令回忆变得支离破碎,真假难辨。站在百叶窗之前,透过窗户向外窥探的男子,与不断摄入的女人面孔特写剪在一起,仿佛呈现了一种女人“被凝视”的视觉文本。包括多次女人在男人面前进行表演。而掐女人脖子几乎就是格里耶最钟情的性趣味了。车祸-公墓-死亡。一切全都是假的。 |

|
交错的记忆与幻想用视听语言来表现挺好的,前边那么多铺垫,结尾的角色互换也就理所当然 |

|
去年在伊斯坦布尔 |

|
影片的三个主要角色都具有符号色彩。男主代表的外国人,来自jd教文明,带着自由的色彩。而女主代表土耳其女性,即ysl世界的女性,她希望男主能带给她自由。女主丈夫代表的是ysl世界的男性,他扼杀着女性的自由。影片的故事可以简单概括为女主被土耳其丈夫束缚着自由,于是他选择身为外国人的男主追求自由。但她发现在获得自由的同时,被男主逐渐控制,于是选择逃跑。男主不断追寻终于再次找到女主,两人开车奔向自由。但由于女主丈夫的阻挠,女主车祸身亡。但实际上是男主想要再次掌控女主获得自由的权利,抢夺方向盘造成的车祸,男主也因为这种控制受伤。女主终于成了一幅画,被男主永远控制。男主开车逃离城市,但是女主丈夫再次出现,男主被控制反噬,在车祸中丢掉了生命。最后女主出现在船上,暗示着女主对男性世界的反抗后获得了自由。 |

|
《去年在伊斯坦堡》所以說,敘事者是說謊的男人....還有女人?(1.多處使用車禍畫外音做為意識流的轉折。2.那些靜止的影像雕像,恍如夢境。) |

|
要是彩色片多好啊 |

|
旅游观光片吗?没有解说。爱情片吗?莫名其妙。悬疑片吗?故弄玄虚。 |

|
相当惊喜。同一场景中不连贯剪辑与不同场景下的连贯剪辑;每个路人都在持续紧盯主角抑或镜头,营造出不可言说的高压;语言、性别、城市、历史、身份,成对出现的片段,均在尽力模糊真实与幻想的边界,以服务“假”的主题;但刚刚列举的这些,似乎又有十分明确的现实指涉,而非仅仅传达理念而已,但终如本片中那位“不朽的女人”之谜一般,不可再索解。 |

|
84/100 无疑与《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像是同一个谱系下的,格里耶执着于描写一位痴迷的男性和一位作为迷本身的女性,当然这也是《迷魂记》式的,在这里面孔和身体被稍微放大了,如肖像画一般。外部而言,带有殖民色彩的土耳其环境与音乐、声音、剪辑提供了某种异域、异样的、不稳定、超现实的空间感。叙事仅仅作为细碎的图像空间结构,而“什么是真实”、内在的秘密仅仅是游戏的部分规则而已。 |

|
相遇-相识-寻找-重遇-死亡,导演彻底摒弃正常叙事、使用形式主义风格的镜头将关于现实与虚构、真实与谎言的内容呈现出异常美丽的结果。在他人最痴迷、最深爱的时候,神秘的消失或死亡,便成了他人生命里不朽的存在。 |

|
假若仅仅只关注符号本身,格里耶的在场将毋庸置疑。但正因为他的旅行,他的伊斯坦布尔记忆,让他得以肯定自己无法留存于伊斯坦布尔之中。如果不是如此幸运,格里耶势必得去寻找一个伊斯坦布尔般的演员,比如许多年后的Bruno Ganz。 |

|
女主好看,喜欢这种真真假假的感觉,说像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其实快不记得这部,想起了阳炎座,但是摄影还是喜欢阳炎座,可能彩色吧。两个女人,前半部分出现的意象到中间故事上明朗了一些过后再重新出现意象,最后女人在船头望着镜头结束,和阳炎座像的一点是两个女人,结构,景也不是很多。再喜欢的形式也会被称作意识流,哎 |

|
如果目光所及之处总是显得过于静止、过于怪异,以至于想象中的几何形状反而推翻了我们的“亲眼所见”,那正是因为目光的那一边(在其间,有一次剪辑...)是真实,而真实相对于现实总是一种过度,正如正午的阳光(我希望这种说法不像是一个比喻而更像是举例,毕竟我是在评论罗伯-格里耶的作品),过曝、刺眼,在这种过度面前,我们失去了言说的能力,以至于除了说谎外无法作出任何行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静滞的东西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总是过快的。 |

|
“你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不是一个真实的城市” |

|
缓慢横揺,水平镜头,大远景,镜面拓展叙事空间,人脸特写至剥离一切审美,只剩下赤裸裸的虚幻在引诱。追忆一次不存在的邂逅,悼念一个从未降生的女子,在那些被掏空血肉的,历史化的人员中躲闪,迎击。两种时态同时出现,早逝的语言回到当下,而当下同时出离进飘渺的过去。虚拟与现实,过往与此在统统脱落,陷入去差异化的统一形态中,失落又寻觅。如同伊斯坦布尔的断壁残垣,好似聊无变化,时时刻刻在铭刻历史与真实。这是与虚幻的女人的互文。她从未出现亦从未死亡,他是静止的伟大的宁谧,所有情绪,文化,历史都好像源自从她的眼眸中的倒映,如此,是为不朽。 |

|
作为《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编剧,格里耶的这部《不朽的女人》处处都是《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影子。雕塑般矗立面无表情的人物,尤其是在女人失踪后,男人不断的寻找,曾经和女人在街头巷尾游荡时遇见的商贩或熟人等等表示都没见过女人,而后在某一个时刻男人在苦苦寻找中终于在街边遇见了失踪已久的女人,这时街道上所有路人都保持姿势矗立不动,如同定格一般,这完完全全就是《去年在马里昂巴德》里上流酒会场景的再现。在影片开始不久时,格里耶运用了别致的转场方式,通过突然出现的人物身体与移动或推拉的镜头相交待整个画面被遮挡时转场到下一个画面,下一个场景与空间,这样的转场方式出现了三到四次左右。 |

|
如此不朽的不可靠,什么都不是真实的。 |

|
与去年在马勒戈壁,啊不,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一脉相承。当然相对去年来说还是相对友善一些,也弱一点。不过调度还是点赞的。悬疑吊打今年某爆款Beoning |

|
格里耶: 超乎寻常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在交错的时空中发生冲突 |

|
在充满神秘的东方国度里,探寻两性之间隐秘的情感关系。在格里耶看来,语言、文本、两性本质上相同,最终的归途依旧是循环往复的神秘主义,在不可得却又偏执的追求下,只会呈现虚伪的存在和真实的死亡。 |

|
确实有点去年在伊斯坦布尔的意思但还是不同只是依旧很法国。存在于不存在已不重要。 |

|
女人是魔鬼,她们擅长做爱。持续的追寻,模糊的记忆,相异之名,情节的不纯粹性。当心,你对这个国家不够了解。没有唯一真实的话语,没有真相的真相。不朽的女人面前,男人只有一个下场。黑白双面人,纵使梦一场。瞬间消失,除了我,所有的一切全部静止,抵抗死亡的唯一方式。雕塑般的路人,风格化的诗意影像世界。突入其来的死亡,是梦非梦,现实非现实超现实,混沌的意识世界,多重嵌套的梦之梦。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今年在伊斯坦布尔,伪造的监狱,伪造的城墙,伪造的故事,你无处可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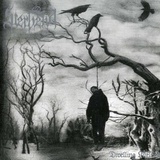
|
看的是无字幕的,实在看不懂,只觉得很诡异,与导演的其他作品风格差不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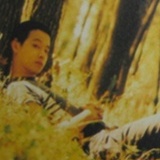
|
~In Stock~[这一切,似是尨乱的酲梦,似是百叶窗前瞑视的作家脑幕中构思的舛文,似是迷离惝恍的伊斯坦布尔湍泷的时空.格里耶在电影文本性中赜探隐索,将交错式的时空结构穿贯于线性叙事中.段落之间以意象(老人&椅子/男孩&敞篷车/窗/墨镜男/渡船06:15)和动作(顾视/俯瞰/转身)为内在联系,辅以逻辑因素07:11/09:05/13:01/22:31/窗-25:39&27:55/33:08/39:44、主观镜头07:24/09:05/14:47、相似主体25:19、拖声39:14、运动镜头41:36、挡黑镜头10:05-11:20等转场技巧敛息环境遒变时观感上的突兀.车祸后开始使用意识流将前情再现并续写,达成"现实"和"想象"的闭环.而摇镜戏法、重复蒙太奇、刻意伪饰的调度以及表演(42:30/75:22/82:40)的运用,给全片刓隐的剧情又蒙上一层蜃氛,更显迷人,当得"神片"二字.] |

|
渐入佳境的电影。声音对画面的过渡与裂痕般的剪辑提供了独特的叙事节奏所以并没有觉得僵硬,时空在此被给予虚假的确证,没有人能逃出这个谜。 |

|
有一部形式使劲为理念服务的片儿,奇诡的视点变化,背景带表演性,人物自带雕塑感,真真假假现实与幻觉现代主义母题探讨,在那个对形式如此狂热的时代。后来去翻了格里耶一本小书《快照集》,惊觉我靠不要太难看吧,形式天生还是更适合影像。 |

|
完全没有时间概念,时间就像男主角一样,被导演揉成一张废纸丢弃。而没了时间概念以后,继而丢失的就是因果。故而导演将整个电影的叙事架空了,并且通过百叶窗的特效,明确告诉我们女主是通过男主时间窥见的。而这个女主角,她时而圣洁,时而淫荡,可她究竟是真实存在,或者仅仅是思维的臆想,似乎观众和男主角一样迷茫,故而我们通过导演的镜头一同去寻找。不好说导演表达了什么,但从路人一致投来的目光(这目光既是看向男主,更是看向我们所有人,而我们就像是做了坏事一样成为目光下的焦点),清真寺里的“女人不洁”的对话,以及许多歪歪扭扭的男性象征的石桩,结合这个片名,不朽的女人似乎指向的是所有男性幻想的“可盐可甜、又纯又欲”的、被窥视的女性。 |

|
美人,内衣,丝袜,铁链,床,掐脖子,格里耶很爱这一套嘛~:) |

|
法国文艺悬疑片,一个曾经消失过的女人,后来她死了也不知道她是谁的女人。叙事手法甚至可以称为前明日边缘系。
虽然女主不算很有味道,男主更是可怜巴巴的,但罗伯格里耶真是很超前啊,甚至有更早的“让我们一起重新开始”,可惜她说“你觉得你够坚强吗,别太那么自信”。
想知道土耳其现在还是片中这么好看吗
2017-10-29 22:59:38 |

|
部分认同老何的观点,算是马里昂巴德的雏形。视觉带着幽灵式的凝视,但这个幽灵是主角被抽象出来的一部分,与林奇这类的梦境大有不同。表演处理得还算生涩,毕竟在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视觉的情况下男主表演得比较外在。而人的静滞、碎片的回忆拼凑不够精致,算是比较生硬直白地告诉你:一切都是假的。 |

|
死亡之梦,欲望的镜像 |

|
剪辑很有意思,构图很美,重复镜头,似真似幻,对白像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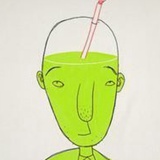
|
288/365days。格里耶的《去年在伊斯坦布尔》,与编剧的马里昂巴德可算是对照文本,同根同源。真实的迷幻本质是,越多次数的回想,就会越美化记忆本身,重又创造出一个不停寻找真实的记忆迷宫,是不断重塑和解释记忆的过程。迷宫里的建筑符号不重要,沦为背景的雕塑人物不重要,那些趋向滞缓和重复的镜头,是现实时空的停止,当死水被打破,所有动势都精准无误地通往一个女人,在被定格的那个时间里,她永远不朽。另外一个感受是,甚至不是感受,是看到,在构筑的梦境中,那些象征本我的雕塑人物,在不可避免,又竭尽全力地晃动着。 |

|
主观真实的意识奇旅,极具文字感的实验影像,亦真亦假,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人物,地点,时间,记忆……记忆与想象交叉融合,碎片的解构再组合最后模糊;
与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辉映成趣,光影的运用,对称的构图,人物走位与空间,声画分离,叙事的心理与客观时间,最为惊艳的是人物的突然插入配合剪辑达到人物走位的转场,以及静止的人物与运动的场景 |

|
故事还是那个调调,但雷乃在行文(行影?)上要微妙太多了,即使《马里昂巴德》也没有这么工整,罗布-格里耶明显强调结构多于人物和情感,这一点本身并没有错,但这部影片的层次还是可以更丰富一些。 |

|
8.5+ 無疑是馬裡昂巴德的姊妹篇,各種意義上的。非常猶疑曖昧的態度,由不止不休的重複呈現,在體驗中凝聚驚人的顛覆性力量——事實上這種精巧的構思已經超脫時空觀因果律以及各類驅動機製固有的結構。男性主導把玩的內窺鏡與東方主義視角相互掩映,其實是對不可求之高度時效性的有限之物的失落而仍富激情的探尋。這當然關乎記憶,但卻不應只著眼記憶,記憶具備一種流動性,縱使其的確被珍藏但儲藏容器——不存在這樣一個具象化的容器,必然是無實體的,必須被強調的是“經驗”的“時期性”成功與“時間性”失敗,二者都是必然的。一個極具欺騙性的片名,也可理解為某種暗示——“朽“自冠以“不朽”之刻始,更遑論一個用於指涉個體的集體名詞了。渴望擁有需適時遠觀,傾聽大地,再極目遠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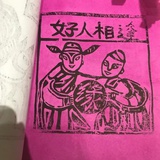
|
这不确实应该叫”去年在伊斯坦布尔”,整个故事实际上是这个男人的幻想,就是他开始问中午的时候,实际上女的并没有带上他,所以接下来就是他的想像。一个男性的欲望故事。 |

|
马巴德和八部半结合体但小于二。唯一可窥的伊斯坦风光欠缺呈现力道,更多情绪飘渺在大量实验镜头、音画分离中,探寻时空结构同时把共情感悬置了。宴会、观众亦如马巴德。墓地联想八部半,全片的游魂感也与之相似。静物人像如玛格丽特的画。
百叶窗幻想媒介,男人主体,女人客体,伊斯坦布尔场域。与原著应补充着看。想一窥清真寺风光不如去看瓦尔达。
脸部特写,人物诡异走姿,身体器官成为摄影机运动的外延。清真寺内舞台般的打光。重复出现的成为能指符号。女人活没活过,死没死过,幽灵一般。
讲悬疑故事呈现的手法是很具实验性的,也挺有意思。通过相同机位角度探索蒙太奇和影像结构。叙事时空制造破碎感,像是把原序影片剪碎重排了。
结尾女人放肆大笑。如果拍日本老城应该也很有意思,背景乐一度让我想起黑泽明的梦。左岸派但层次可更丰富。 |

|
一部完全作用于认识论层面的电影,因其本体的经验在重复和差异之中完全失去其实在的证明,在意识不断的跳跃与错位中,影像中的时间被解构和降维(去时间化),成为非时间的碎片,也就是记忆-感知-意识-现实被处理为一个混沌的全体,成为了影片的主体,它们在电影时间中不断的变形和扭曲、按照黑色电影三幕式的结构发展,而真实的时间在影片中却成为被寻找和永远没有在场的对象。最印象深刻的是影片处理创伤的方式,那是一种记忆不可避免的回溯,在重复之中带来真正的创伤和毁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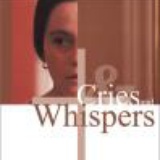
|
格里耶的意识流精湛到了无形。不存在的女人,幻想的艳遇,虚幻的伊斯坦布尔,怪异的人群,一切都是徒劳,深深的虚无主义 |

|
土耳其沧桑风情中的历史幻影,在文化废墟中徜徉迁延。角色在不同空间中出没,压缩了历史时间的长度,她的鲜活在断壁残垣中鲜明到虚假,恍如隔世。同时她也是符号和情绪,刻意构图、冷静的疏离、寻找她的悬念加强了人物经历的虚幻性和时光的流逝感。 |

|
一种《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再现,格里耶所讨论的还是记忆与意识对于现实的主观侵入,在这种主观之下不管女主还是他所留意到的任何人/事物都被平面化再赋予某种臆测下或者情感的印象,从而使整个外部世界的真实性产生波动,此时真正的真实仅存在于角色内心,而透过他眼睛所展示出的只有无尽的幻象。
横移镜头/海/偏移的视线/对称构图与段落/镜子/回忆与虚构。 |

|
感觉一个人长期处于出神、幻想、回忆、颠倒中是一件特别费钱的事,一定要无所事事,衣食无忧,还要身体好,营养充足。不然很容易挂掉。再加上幻想的画面还那么美那么高级,而不是什么B级片似的下三路,那就更费钱了。哇,这不就是法国版的贾瑞照风月宝鉴照死的故事吗。最后一个镜头法版熙凤的狞笑。 |

|
罗伯-格里耶认真起来也能拍好电影,他的同名小说完全就是分镜头剧本,可看作《去年在马里安巴》的姊妹篇,电影甚至有受其影响的痕迹。都喜欢在虚构与现实间使用意识流转换,也一样有刻意安排的静止动作。几个空镜头不错。 |

|
由个体“身份焦虑”出发,剪辑意在重构“人脑思考的过程”,从清晰到逐渐乱序,在不断思忆追寻中,“真”和”虚”的界限在慢慢变得模糊,以此引出连串质问,思辨,我们的记忆,所生活的世界,是不是确切存在的?格里耶完成了一次用影像书写哲学的命题,“凡是所有相,皆是虚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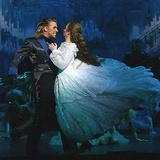
|
是美的。
但将一个女人的美、性感和神秘混为一谈的做法实在让人有些烦厌了。或者说依然是那种极其刻板的男性想象中的神秘女性形象,那种老套的神秘女人离开,男人惊觉恍如梦一场的故事。美得不可方物,狂野得好像超脱了各种道德体系的束缚,一个完美得本该不存在的形象,当然也会让人怀疑她是不是真的存在。
台词中反复强调“一切都是假的”也有些累赘,和后半段寻人过程中的各种设计一样僵硬。 |

|
去年在伊斯坦布尔,弱叙事的艺术电影。
1、“莫名其妙的失踪、忽如其来的死亡”两个情节宛如乐章的顿点,用男主人公寻找的动作叩问事实与记忆、真实与虚构、真相与假象之间的边界,用镜头之间的无缝衔接进行时空转场,流畅地在各个场景中穿梭,同一主人公先前在室内下一秒就出现在海边,且人物的先后动作并无明确连续的逻辑关系,而是断续、自由的跳跃。
2、“凝视/窥视”屡次出现,男主角透过百叶窗看楼下女人的视点镜头、土耳其女郎在一群男性注视下的舞蹈表演(与安东尼奥尼的《夜》如出一辙)、女主角的舞蹈等画面均显示出这一点,而影片首尾女主角面对摄影机眼睛一眨不眨、带着神秘微笑的镜头使其宛如一具美丽的人偶,仿佛带着死亡般的神秘,而之后缠绕的记忆将男主人公引向死亡,似乎验证着黑色电影中已显示的蛇蝎美人的致命效应。 |
![豆瓣评分]() 8.1 (705票)
8.1 (705票)
![IMDB评分]() 7.2 (1,424票)
7.2 (1,424票)![烂番茄新鲜度]() 烂番茄: 86%
烂番茄: 86%![TMDB评分]() 6.79 (热度:3.87)
6.79 (热度:3.87)






























